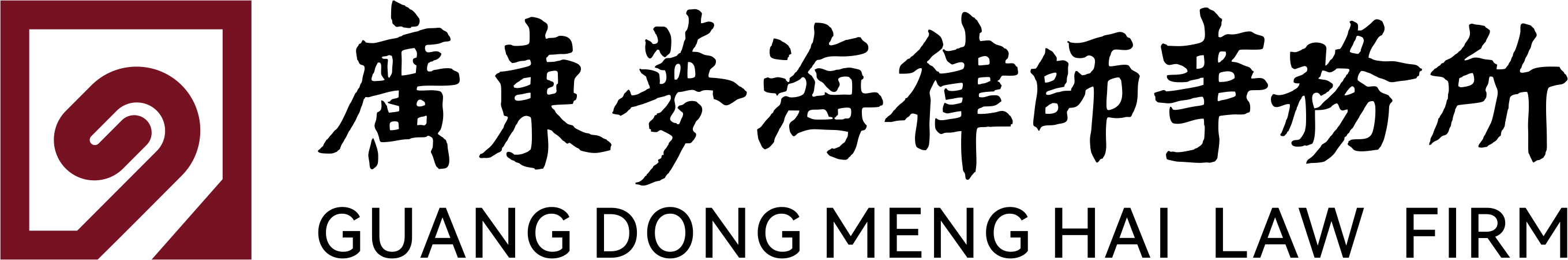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司法适用—基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再思考
一、概念、范畴及界定
(一)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标准
1、“证明”的问题。
关于“证明”的问题,英国学者威廉·涅尔曾指出,“我们可以区分三种能找出证明和要求证明的论说类型:在纯数学里,我们寻求证明先天抽象的真理;在形而上学里,我们寻求证明关于世界结构的最一般命题;在日常生活论证中,尤其是在政治或法庭上的论证中,我们寻求偶然性命题的证明。”由此可知,在威廉·涅尔看来,法庭上的论证作为司法上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过程问题,它首要属性是生活性的,是立足于日常生活而来的“证实”;同时,这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必须立足于个案而论。这对于本文论证,将起到一个支撑基础的作用,本文的很多论断,将由此而引发。
2、“司法证明”的问题。
关于司法证明,有学者认为是“司法人员或司法活动的参与者运用证据明确或者表明案件事实的活动。”从严格意义上看,这样的概念界定只能是一般性的,并不能完全严格限定“司法证明”的内涵,因为司法证明的关键在于证明主体的问题,从遵从一般诉讼规律角度看,司法证明的主体应当包括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审判人员只能作为自向证明的主体,而不能成为他向证明的主体,这是基于审判中立性的要求。换言说,审判人员只能是证明活动的被说服者,而不能是说服者。
3、“司法证明标准”的问题。
何谓证明标准,定义表述迥异,有学者指出,所谓的司法证明标准,实际上系客观模糊性、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混合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任何尝试对“司法证明标准”作出精确定义的努力都将白费功夫。而一般性的界定,则更大程度上增加了对其准确把握的难度,并对司法实践造成更大的“迷惑空间”。如有论者指出,司法证明标准,就是指“司法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和水平。”《布莱克法律词典》亦尝试对此作出界定,指出司法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如何使证据确信而必须达到的状态。主要证明标准有:排除合理怀疑(只用于刑事案件)、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据、优势证据”,但无论怎样,这些尝试性的界定至少在概念范畴上为提高认识的精准度作出了应有的尝试,并在相当程度上为避免司法实践走进更大的认识误区提供了试错空间。
4、“刑事证明标准”的问题。
就一般意义上看,刑事证明标准就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相关参与主体“实现查明刑事案件客观真实任务的具体指标”,系作为“必须的”“判断对错的尺度”“与案件真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存在形态。由此可见,刑事证明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中论证的重要形式,其在偶然性命题下的尺度,其实是在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用一句生活性的话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雾里看花的过程,司法裁判者只有拨开层层迷雾,才能发现案件的真相,而这个过程所指向的“彼岸”,则是由法律先定的证明标准来规制的。
(二)为什么需要刑事证明标准?
1、尊重制度理性的要求。
不难理解,刑事司法过程其实就是司法裁判者不断发现事实真相,进而进行刑法评价的过程。这个过程,司法裁判者主观之于客观的能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为了防止刑事司法认定犯罪事实的裁判者的主观性不至于走向任性,必须对犯罪事实的裁判者(陪审团或法官)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观心理活动设定一个必要的约束或者限制。”只有将个人理性限定在制度理性范畴内,或者说,将个人理性建立在制度理性基础之上,才能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当性,才能真正以一个理性人的司法判断认定某一业已证明的犯罪事实为“真”。
2、遵循诉讼规律的要求。
前文已指出,无论怎样限定刑事诉讼过程的证明要求,刑事诉讼的证明都无法避免模糊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混合”。
就其主观性与客观性而言,这是基于认识活动规律以及个体心理活动规律作出的常识性判断,此不赘述。
而就模糊性而言,作为生活命题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首先是对偶然性问题的回应,而这种偶然性,是难以用数学理性来界定的,亦即无法用精确的数字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模糊性标准反而应当成为标准的一种类型”这样的判断并非没有正当性基础。
另外,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一针见血指出,法与法律制度是纯粹的语言形式,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法律语言与概念的运用,法律文本与事相,立法者与司法裁判者基于法律文本的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等等,都离不开语言的分析。
由此,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自然也离不开语言。但与此同时,法律语言跟其他任何语言一样,都具有天然的模糊性,任何语言的精准其实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的,这样的判断已在众多模糊理论著作中得到研究证实。
而在一般的认识论上,则可以从《圣经》中得到深刻的启发:旧约《圣经》中《律法书》“创世纪篇”中关于“巴别塔”的论述中指出,由于众人“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要分散到全地上”而冒犯了耶和华,耶和华就“在那里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因此,在法律语言环境的模糊性天然存在、司法裁判者内心判断的主观性无法避免的现实困境中,刑事诉讼要做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如果放弃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诉讼结果的追求,又将使整个刑事诉讼变得毫无意义,毕竟,“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关于犯罪事实认定都在尽可能地追求一种确定性或者客观性”,而要追求这种确定性、真实性,首要的前提就是解决前述司法裁判者主观活动走向任性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设定先定的某种客观要素标准,限制司法裁判者的主观恣意与任性,这种标准的确定,在符合刑事诉讼一般规律要求前提下,就成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3、经验理性的可能。
任何标准的确立,其实从中心词域考察,都离不开对“信仰”的坚定。如从基督教信仰上看,对上帝的“信”构成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这是前置性的问题。回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必要性问题,其前置性的问题则是,对法治的坚定信仰。
在此基础上,采取怎样的信仰进路,那是多维度的。如有学者通过对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渊源进行考察,认为经验哲学家洛克对于刑事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分级,其通过“排除合理怀疑”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具有正面意义”,并认为“它的具体操作需要参照对案件的调查结果的‘心理描述’状态谱系,它的功能发挥需要经验理性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看,经验理性的态度有其可取的地方,特别是在司法裁判者囿于案件真实发现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在特定事实认定难以判明的时候,刑事证明标准刚好提供了一条先定的法律路径依赖,一种接近司法制度理性的依据,也为司法裁判者着眼于偶然性的个案判断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另外,经验理性的可能性也为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中面临操作疑难问题时,提供正当性依据。毕竟,“在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或者逻辑判断相反的情况下,追求不同于日常经验或者看似矛盾的确定性认识,不仅需要很大的实践勇气,甚至要忍受来自社会不同层面的批评和质疑。”而这些质疑,本来是先定的刑事证明标准所无法解决的,但由于司法裁判者经验理性的存在,使得这些表面上是对案件事实认定、间接上实际是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否定的批评能够包容在司法裁判者经验理性所做出的判断之中,也从硬币的另一面证成了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必要性。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理念分野与殊途同归
(一)理念分野:纷纭复杂的刑事证明标准
1、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系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中采取的证明标准,同时对中国影响颇为深远,在刑事法学界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尽管如此,在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界定问题上,却颇为周折。因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表面上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那些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其困难。”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罪行必须被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方能成立,意思是被证明的事实必须通过它们的证明力使罪行成立。”
上述解释,其实并不足以对排除合理怀疑作出精准的界定。在判例具有与制定法同等重要,甚至比制定法具有更为深远影响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法官在个案中的解释也许更具有说服力。
如丹宁勋爵(Denning)于1947年在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 一案中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已经确定。它不必达到确定性(certainty),但必须达到很高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不是排除怀疑阴影的证明……如果指控的证据很有力,只是有极小有利于被告人的可能性,就应当以‘当然可能,但一点都不合理’这样的裁决驳回这种可能性。案子就证明了排除合理怀疑,但是任何低于该程度的证明都不够充分。”
而在美国,合理怀疑最为接近精准的解释恐怕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的表述:“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的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态处于这种状态,他们不能说他们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而排除合理怀疑,则是陪审员的心态已经达到前述内心确信的状态。
2、内心确信
内心确信,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通常性表述,法国最先将其刑事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规定为“内心确信”,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法官必须根据庭审辩论和各方争辩的材料,作为内心确信的依据……法律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的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经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德国、比利时等国家也使用内心确信的表述。我国台湾地区沿用中华民国1935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之。”此后条文虽多有调整,但内容一致未变,至2003年9月生效实施的台湾《刑事诉讼法》第155条明确了内心确信的概念,规定如下:“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伦理法则。”由此在承认经验理性以及伦理法则的规制下,赋予法院法官个案判断时在自由心证基础上达至内心确信的裁量权。
3、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这种表述见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可以理解为法定的刑事证明标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①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②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③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与此同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做了如下限定:
①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③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根据相关立法解释,前述“排除合理怀疑”指的是:“对于认定的事实,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了确信的程度。”
(二)殊途同归:刑事司法证明的现实需要
1、为什么会“殊途同归”?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司法判断主体本身。无可否认的一点,无论采取怎样的刑事证明标准,归根到底都是要求司法裁判者(陪审团或者法官)在案件事实认定上,作出具有说服力、经得起怀疑和批评的判断,在这个层面上,无论是排除合理怀疑,是内心确信,还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都没有根本区别,甚至基本上具有等价的意义。
因为,若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去衡量某一偶然性的个案中所需要认定的犯罪事实,那么从司法裁判者主体上看,他肯定需要达至内心确信的程度,否则他做出的判断甚至无法说服自己,更遑论得出的裁判结论能服众,而这在事实上考察,恰恰又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体现。
这就是众多证明标准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其核心意思都是等价的原因所在,因为“所有的证明标准,无论表述得多么像一个客观的标准,但其实这个标准最后都必须转化为犯罪事实裁判者主观心理的标准。”而这种“犯罪事实裁判者主观心态标准”的正当性来源,事实上是通过事实审理者,在主动探求案件事实、竭尽所有证据材料后,在经验理性指引下作出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包括前期对刑事证据的判断,绝不仅仅只是事实的,同时还是道德的。
因为司法个案的判断,就是“我们寻求偶然性命题的证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司法裁判者的思维过程是怎样的,其实并不重要,对于利益攸关各方来说,最终的判断是否令人信服,反而才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如此众说纷纭的刑事证明标准,就此殊途同归,要求司法裁判者弃却主观恣意,放下权力傲慢的姿态,在我国当前“当事人缺乏信用、法官缺乏信念、整个社会缺乏信仰的支撑”的艰难困境中,基于经验理性的要求,依赖法治信仰和道德,树立起回答“偶然性命题证明”正当性问题的威信。
2、为什么我国刑事立法选择“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
①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③结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对此,有人指出,对于排除合理怀疑,主要是“要求我们审视疑点与矛盾认识的合理性,要求我们的证明力思维和案件事实认定进一步精准化,然而,事实认定中的最基本的判断,仍然基于‘常识、常理、常情’的经验判断。”
在司法实务价值判断层面,现行《刑事诉讼法》通过立法的手段,增加前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认定条件,无疑是间接引入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但是,合理怀疑作为一种“难以决定(hesitate to act)”,“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moral certainty)”和“很高的可能性(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在司法实务中依然具有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因此,如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依然是在一个个偶然性个案中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如有论者指出,认定犯罪的途径,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证明的肯定,亦即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且据以定证据经过庭审中举证质证,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另一个方向则是反向认定,亦即排除合理怀疑。这是一个新颖的视角,并且在司法实践当中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由此可见,之所以将“排除合理怀疑”规定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必要内容,首先是因为刑事证明标准的必要性所致。深层次原因则是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作为单纯的刑事认定标准还是案件事实的反向认定准则,其证明排除合理怀疑是可能的,并且是很高的可能性,将使得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而归根到底,在我们现在“面临的完善证据立法和司法这两个现实任务来说,重要的就不是给证明标准改革什么名字,而是为其确定所需、所能、所应借鉴的相应的配套规则。”
因此,深刻认识刑事司法中证明标准的涵义,是“一切回归实践”的要求,也是“司法”这堂“实操课”的中心话题,但需要司法人员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在每一个司法个案中作出体现法治信仰、道德的判断。
三、为了个案正义:如何准确“排除合理怀疑”?
(一)为什么要“为了个案正义”?
对于个案正义的重要性,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在《论法律》一文中有过深刻的论断:“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江必新曾发表文章称:“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基本价值追求,是社会公平正义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而实现司法个案公正又是实现司法整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案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更不用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由此可见,个案正义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而个案司法不公其后果将比犯罪本身危害还要大得多。
而早在2013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而现实的问题在于,个案的公平不是可以通过喊口号就能实现的,而需要每一个法律人从中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更甚者,当前中国的司法实务界“一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充满权力的霸道,严重漠视当事人的合法诉请,似乎他想怎么认可就可以怎么认可,想怎么判就可以找到什么证据来判,证据的取舍、证据规则的运用基本根据‘案情需要’,司法诚信在当今社会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
更为极端的后果在于:“有些人不信任和信仰法律,不是因为他不懂法才不相信法律,而是因为他懂得了法律、经过了法律诉讼之后才不信。”
因此可以说,一旦法官滥用司法权,则司法的公信力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在刑事司法领域,如果法官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未能得到合理的规制,则使个案正义无从谈起。
(二)个案中排除合理怀疑简析
1、周某某非法持有枪支、爆炸案
(1)基本案情:①非法持有枪支犯罪事实:被告人周某某以12000元价格,从他人手中购买仿六四式手枪1支以及对应型号的改制枪弹20发,后将枪支及子弹藏匿在XX市XX区XX镇XX村暂住处。案发后被公安机关收缴。②爆炸犯罪事实:被告人周某某与XX市XX区XX镇XX村村民郭某某相识多年,并在XX村一处房屋居住。期间因房屋拆迁补偿,双方就房屋产权归属问题产生矛盾。被告人周某某后怀恨在心,产生杀人之念,并购置爆竹、钢珠和单刃尖刀、帽子、口罩、打火机等物。后被告人周某某用报纸包裹剥离出的炮药并密集黏附钢珠,自制成全长18.4cm至21.8cm不等圆柱体爆炸物10个。某日18时许,被告人周某某携带手枪、自制爆炸物等作案工具,潜入位于XX市XX区XX镇XX村郭某某住宅院内,见郭某某与家人李XX、郭X全、刘X云、郭X宝、郭X健、杨XX、郭X堉、郭X乐及郭X宝朋友杨X等人聚集屋内准备过年,便将二个自制爆炸物先后点燃后投掷室内并爆炸,致屋内家具、门窗玻璃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并致郭某某、郭X全、刘X云、郭X堉等人身体不同程度受伤。爆炸发生后,郭X全、郭X健、郭X宝、郭X乐、杨X等人出屋追赶欲逃离现场的被告人周某某。被告人周某某在逃跑过程中将装有八个自制爆炸物及尖刀等工具的挎包丢弃,后持子弹已上膛的手枪对郭X全等人射击,由于故障子弹未能射出,后被郭X全等人抓获并报警归案。
(2)本案需要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本案中,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周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周某某有非法持有枪支的事实,同时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时即有侧重地讯问犯罪嫌疑人周某某故意杀人行为的经过,忽略了其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经过的侦查,不能确定其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系单独的实行行为还是故意杀人行为的准备行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并可能影响案件的定性。
后经退侦查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系基于个人对枪支的喜好而从他人处购来枪支,购买枪支半年后,实施爆炸行为半年前,周某某还曾前往被害人郭某某家中,就房产归属问题进行交涉,那时犯罪嫌疑人周某某尚未产生杀害郭某某全家的想法,自那次双方交涉未果后,犯罪嫌疑人周某某方产生了报复郭某某全家的犯罪意念。
故此,可排除周某某非法购买枪支并持有的行为系故意杀人行为的准备行为之合理怀疑,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爆炸罪追究周某某的刑事责任。最后,法院一审采纳了前述分析意见,当事人一审服判,未上诉。
2、张某某抢劫案
(1)基本案情:①某年某日20时许,被告人张某某伙同齐X波、王X、代X军、赵X余、“小江”预谋抢劫并事先准备好弹簧刀等作案工具,后由齐X波、赵X余驾车来到XX市XX区XX里附近,寻找、确定抢劫目标后驾车离去。当晚21时许,被告人张某某伙同代X军、王X、 “小江”骗租XX市XX区XX镇人邢XX的汽车谎称去XX区XX镇XX村,当被害人邢XX驾车行至XX区XX镇XX村附近时,被告人张某某与代X军、王X、“小江”等人以持刀威胁、掐颈、拔车钥匙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邢XX佩戴的黄金项链一条。②某年某日21时许,被告人张某某伙同“洪雨”、齐X波、王X、代X军驾车来到XX区XX超市附近,见出租车司机祁XX在车内等客,便产生抢劫之念。后由王X、“洪雨”骗租祁XX的汽车谎称前往XX饭店,当祁XX驾车行至XX饭店附近停下后,在此等候的被告人张某某打开司机一侧车门,与代X军、王X、“洪雨”等人采取按住被害人祁XX双手、持刀威胁等手段迫使祁XX屈服后,当场劫取黄金项链一条、苹果4S手机一部及内装现金人民币600余元和银行卡等物的棕色钱包一个。
(2)本案需要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形: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洪雨”不在案,公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抢劫作案三起,第三起系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洪雨”两人合谋作案。但对于第三起抢劫事实,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自侦查阶段即不予承认。
辩护律师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后,经阅卷发现,认定该起事实的关键证据——被害人陈述中虽证实系两个人协同实施抢劫,但在辨认过程中却未能准确辨认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对于该起事实的证据尚存瑕疵,未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后经申请退回公安机关公补充侦查,亦未能查实。
综合全案证据,辩护人认为对于第三起抢劫事实,由于证据本身存在瑕疵且无法补正,合理怀疑无法排除,不能作为认定该起事实的证据,遂将相关辩护意见提交至检察院。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张某某第三起抢劫事实的证据不足,只认定被告人张某某前述两起抢劫事实并提起公诉。
特别鸣谢
本文写作过程中,作者曾与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纹封律师、争议解决业务部主任王宏亮律师就刑事个案证明标准问题进行过多轮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对刑事法律实务中存在的“每个办案部门都有一部刑事诉讼法”“每个案件都有一套证据裁判标准”等痛点问题,两位资深律师给予作者诸多启发。
本文最终能够成稿,离不开陈纹封主任、王宏亮律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龙建林

广东梦海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曾供职于天津市某检察院、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曾先后任检察官、国家公诉人,行政执法员、行政听证员,行政审批主任等职。现任深圳市法学会粤港澳大湾区法治青年研究会理事、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检察院首届听证员。中南大学法学学士,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师从闵春雷教授,长期从事刑事法、证据法等方面理论、实务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