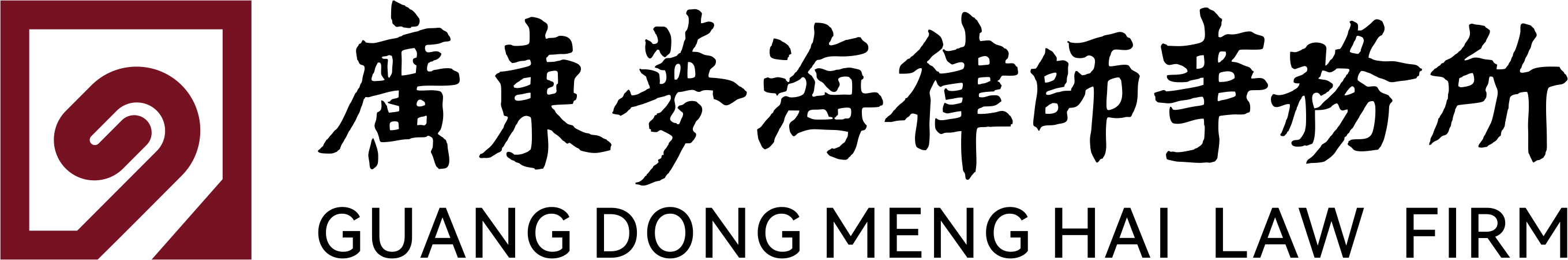债权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的救济路径实务探讨
一、债权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模式的问题缘起
在投融资领域,不管是传统的金融借贷模式亦或是当下火热的对赌回购、差额补足等金融创新模式,投资方多为一些银行、信托、证券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在从事投资、贷款业务时均会要求融资方提供相应的担保等增信措施。纠纷发生时,债权人通常选择向管辖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债务人以及担保人同时主张债权的常规稳妥的诉讼模式。
现实中,债权人出于顺利实现债权的目的,有时却希望先行单独主张担保人担保责任,如在主从合同中约定了不一样的争议解决条款而导致管辖不一致,债权人先行主张担保人担保责任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部分乃至全部债权情形;债务人被起诉后无力偿还或者下落不明,经常会出现不予签收起诉材料以及法院传票或者主张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的情况,从而拖慢诉讼进程,甚至进入到公告送达程序,延长了整个诉讼周期,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顺利实现产生了极大阻碍情形。前述情况下,债权人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主张对担保人的担保财产先行受偿则成为维护其自身权益实现的新思路。
有鉴于此,文章以单独主张担保权利为前提,区分不同的担保模式,对相关法律规范、司法解释结合裁判观点进行归纳梳理,从法律逻辑关系中证成债权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的诉讼可行性。
二、债权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模式的法律规定
(一)单一保证模式
1.一般保证:《担保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一)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
(二)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三)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66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规定:“保证人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有权申报其对保证人的保证债权。
主债务未到期的,保证债权在保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主张行使先诉抗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在一般保证人破产程序中的分配额应予提存,待一般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任确定后再按照破产清偿比例予以分配。
保证人被确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的管理人可以就保证人实际承担的清偿额向主债务人或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2.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二)单一物保模式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物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混合担保模式
《担保法》第28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2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当事人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债务人与保证人、抵押人或者出质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物权法》第176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四)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民诉法解释》第73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三、债权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模式的裁判观点
文章选定当下法律行业比较认可的“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为案例数据库进行检索筛选,鉴于实践中关于单一保证模式和单一物保模式并不多见,我们主要检索涉及混合担保模式的案例,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128条”等关键词进行多次全文检索,然后筛选出“本院认为”部分涉及到能否单独起诉担保人裁判观点的有效案例12则[1],裁判时间多为近三年,其中最高人民法院2则,中级人民法院9则,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1则。12则案例虽然不足以完全代表单独主张担保权利模式的所有裁判观点,但对单一保证模式、单一物保模式以及混合担保模式的单独可诉性都有涉及,通过整理这12则案例的裁判观点,也可以初步总结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模式诉讼可行性的主流裁判观点。
(一)单一保证模式中一般保证中债务人与保证人必须作为共同被告,连带责任保证中则不是必须作为共同被告
在单一担保模式系仅存在保证的情形下,还需区分该担保模式属于一般保证亦或是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仅起诉一般保证人,不起诉债务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担保法》第17条明确规定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同时关于债务人与一般保证人是否应为共同被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66条规定的是“应当”,(2018)粤20民辖终694号案件的裁判观点亦是如此。虽然《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规定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一般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但债权人在一般保证人破产程序中的分配额应予提存,待一般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任确定后再按照破产清偿比例予以分配,这实与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起到的作用基本一致,因此若单独起诉一般保证人时,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若该担保模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关于债务人与连带责任保证人是否应为共同被告,《担保法》第18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6条的规定的是“可以”和“或者”,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这表明已经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赋予了债权人单独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或者与债务人合并起诉的选择权,(2018)渝01民终3194号案件裁判观点中有相关表述。
(二)单一物保模式中应当将债务人和物的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
单一物保模式中,单独起诉担保人时,仅从诉讼的角度考虑,法院应当追加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我们检索出来的12则案例中,各法院对单一物保模式涉及应当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的裁判观点基本不持有异议,如(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案、(2018)京02民初254号案、(2018)京02民初53号案、(2015)鄂汉江中民二终字第00112号案 (2014)庆中民初字第58号案裁判观点中均有表述;但是,个案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特殊之处,如在我们检索到的(2018)粤0303民初25313号案中,因为债务人系有限合伙,而抵押人又系债务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债权人仅起诉抵押人时,债务人实际上也能够完全了解主债权成立、生效、履行等相关事实并可作出充分抗辩,因此法院并未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一般情况下,在单一担保模式中仅存在物的担保的情形下,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1款的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物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混合担保模式中债务人和担保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是指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以及质押人之间的或者关系
混合担保指的是对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抵押或者质押担保的情况,通俗的理解为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混合。坚持混合担保模式中债务人和担保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是指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以及质押人之间的或者关系的有3则案例,其中两则案例为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具体如下:
(2017)最高法民申3941号案认为
在涉案债权既有保证又有抵押担保的情形下,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2款“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当事人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债务人与保证人、抵押人或者出质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规定,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诉讼中,担保人五矿安科公司以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声称已经偿还债务,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实际履行债务情况对查清本案事实具有重要作用为由,请求追加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本案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不参加诉讼,亦能查清案件事实,故担保人五矿安科公司请求追加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不予支持。
(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案认为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2款是针对同一债权上既有人的担保又有多个物保的情况下,债务人与担保人的诉讼地位的解释,该款规定并未强制要求混合担保中的债权人必须将债务人和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列为共同被告一并起诉,而是将选择权交由债权人,在债权人单个起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不能追加债权人没有起诉的其他担保人参加诉讼,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和选择,这一规定符合现行物权法的规定。债权人延河信用社的债权上人的担保与多个物保并存,债权人延河信用社在前案诉讼中已经单独起诉了债务人,虽在前案中未起诉担保人新合作公司,但其作出了明确意思表示不放弃对新合作公司的抵押权,则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其可以通过非讼程序和提起诉讼两种方式对新合作公司行使抵押权。该案中,债权人先行单独起诉了债务人,随后又单独起诉了担保人,说明债务人和担保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是指债务人和保证人、债务人和抵押人、债务人和质押人的并列关系,可以单独作为被告。
(2018)渝01民终3194号案亦持此观点,认为法律已经赋予了债权人在主张权利上的选择权,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及抵押担保责任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范畴,向兴国选择单独向徐巧即本案担保人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且债权人向兴国举示的证据足以说明其与债务人唐多全之间存在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
虽然前述三个混合担保模式案例均存在特殊之处,并不能重现法律规定的理想情形,如在(2017)最高法民申3941号案中,债务人泰安山水公司不参加诉讼,亦能查清案件事实;在(2018)渝01民终3194号中,债权人向兴国举示的证据足以说明其与债务人唐多全之间存在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案中,债权人延河信用社在前案诉讼中已经单独起诉了债务人,并作出了明确意思表示不放弃对新合作公司的抵押权。但是,通过分析混合担保模式的相关法律规定,前述3则裁判案例并无不妥。《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8条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均指混合担保模式,但存在细微差别,28条中的物的担保包含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和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38条中的物的担保仅包含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但均不影响债权人可以主张保证人在物的担保范围以外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要求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物权法》第176条关于混合担保模式进一步明确规定,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规定债务人必须与担保人作为共同被告。因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2款的混合担保模式是指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以及质押人之间的或者关系在逻辑上与一般保证模式和单一物保模式并不矛盾。
四、结论
出于对诉讼安全的考量和查明事实的需要,在先施行的《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单独主张担保权利采取共同诉讼模式,但《物权法》对于混合担保模式的规定内容中并未包含共同诉讼的表述,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关于混合担保模式应当优先适用《物权法》的规定。同时,在(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案裁判观点中,亦有“《担保法司法解释》起草人亦认为此种必要共同诉讼模式相对落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颁布于《物权法》实施之前,因此,在《物权法》实施之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第1款的规定已明显落后于法律规定,该规定显然已经不能符合现代趋势。”的表述。就近年来的投融资领域的发展状况而言,一般保证模式与单一物保模式已经极为少见,基本都是以混合担保模式存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8条第2款的混合担保模式是指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以及质押人之间的或者关系亦或是指债务人与保证人、债务人与抵押人以及债务人与质押人之间的或者关系即便存在法律理解上的争议,但结合《物权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债务人和担保人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应理解为债务人、保证人、抵押人、以及质押人之间可以单独作为被告进行诉讼,换句话说,债权人单独主张担保权利的诉讼模式不存在法律障碍。
[1]为精简主文内容,相关案例的裁判观点嵌入主文,附案号供检索详阅。(2017)最高法民终964号、(2017)最高法民申3941号、(2018)京02民初254号、(2018)京02民初53号、(2014)庆中民初字第58号、(2015)鄂汉江中民二终字第00112号、(2017)内06民再22号、(2019)渝05民终1435号、(2018)粤20民辖终694号、(2016)苏11民终1287号、(2018)粤0303民初25313号。
(特别声明:本文章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陈峰 律师
深圳市信息服务业区块链协会法务中心副主任
执业领域:争议解决、银行与金融、不良资产处置
邮箱:13670210277@163.com